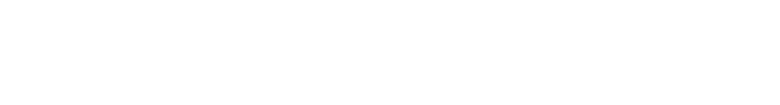[学者笔谈] 符长波:暗物质探测小记
[发布时间]: 2013年01月22日
■ 在人类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下,对这个世界寻根刨底,步步深入,给出了一个又一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答案。
■ 天文学家在这些新的波段内,试图探测那些在“可见光”波段内的“不可见”的暗物质。但是这些搜索都被证明是徒劳,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所处的宇宙大部分是由神秘的暗物质构成。
■ 暗物质探测是目前天体物理和粒子物理的热门研究领域。

人类好奇心
有这么一个广泛流传的关于保安的调侃:每个保安天天都在反复追问三个终极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其实不单单是保安,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小到每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小朋友,都会经常问这些与生俱来的问题。当一个小朋友两三岁时,仍然懵懵懂懂,抑或略晓世事,都会问爸爸妈妈这样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在这种原始的驱动力作用下,地球上每个民族,即使是刚刚步入文明,都会试图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答案缤纷多彩,随历史时代变化而变化:可能从宗教方面回答;也可能从哲学方面回答;到了近代更出现了所谓的科学答案。
例如,就“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答案就很丰富而有趣。中国古代关于人类从哪里来的解释是“女娲造人”。相传女娲根据自己的形象,抟泥成形,五官七窍,躯干四肢,各各分明。放在地上,哈上一口气,居然就活了,并且敷衍至今。就“世界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答案是“盘古开天辟地”。宇宙本自混沌,像个大鸡蛋。盘古这个老祖宗在这个鸡蛋里待久了,感到厌倦了,就一斧子劈开了这个混沌世界。于时“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宗教界对人类起源、宇宙起源的问题答案就偷懒的多,即把所有的不能回答的,都统统推到神的头上。比如基督徒说,整个世界和人类是上帝花六天时间造的。如果你要问上帝是谁,又花了多少时间造的?一般的神学家会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也不能免俗,同样要回答三个终极哲学问题: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其实科学探索这些答案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总是磕磕绊绊,并且很多时候还与神学交织在一起。牛顿,这个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包括万有引力理论在内的古典力学体系。然而晚年的牛顿在研究行星为什么会围绕太阳运转时,把初始条件,归结于上帝,即来自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
然而无论如何,在人类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下,对这个世界寻根刨底,步步深入,给出了一个又一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答案。今天,我们知道,向微观小尺度方向,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质子中子由是由夸克以及其它基本粒子构成等等。我们也同样获知:向宏观大尺度方向,人类居住在地球上;地球围绕太阳运动;根本算不上起眼的太阳处于银河系的一个悬臂上;银河系是无数星系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最初的火球膨胀而来;组成我们身体的氢原子是从这个大爆炸而来,而组成我们身体的其它重元素,碳,氮,氧等,则是由宇宙中美丽的烟火,超新星爆炸而生成的。在人类理性光辉的照耀下,宇宙的每个层次都相当地清晰、甚至是完美地展现出来。
然而正当我们要感慨人类的伟大时,突然发现宇宙中有95%以上的物质和能量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些幽灵般的物质完全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它破坏了历经数个世纪辛勤架构的科学体系。毕竟,如果一个理论体系只描述了5%的对象,实在不能称为好体系。
暗物质问题
暗物质问题最初是由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发现的。早在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Fritz Zwicky在研究星系团中的星系的重力质量时,发现了所需质量至少是发光物质质量的400倍。他称这些不发光的物质为暗物质。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400倍这个数字被认为是高估了,但是这不改变暗物质质量远大于发光物质质量的事实。
暗物质研究的另一重要先驱是美国女天文学家Vera Rubin。在上个世纪50年代,Vera Rubin仅仅是个二十二岁,攻读硕士学位的年轻姑娘。她在硕士论文研究期间,系统的研究了大量星系中单个星体的氢原子谱线。因为多普勒效应,恒星的氢原子谱线会因为星体的运动而蓝移或红移。通过测量蓝移,或红移的多少,就能确定星体本身的运动速度。研究银河系之外的恒星运动,要比研究银河系内的恒星运动容易得多。银河系是圆饼形结构,而太阳系处在圆饼的面上。因此如果要观测银河系里的其他恒星时,近处的星体会屏蔽住远处的星体,从而造成观测困难。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不管怎样,Rubin积累了大量的恒星观测数据,特别是河外星系事例。随着数据的逐步积累到足够多时,她尝试利用这些数据去描述星系或星系集团的整体运动状态。Rubin的观测数据显示,星系或星系团,围绕着某个中心点在运动。这样的运动,不难用万有引力去描述。如果代入观测到的恒星的质量,那么会得出结论:随着星体距离中心越来越远,星体的速度会越来越慢。然而观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使在离中心很远的地方,天体的运动速度并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明显减小。Rubin意识到,必须引入新的质量,即暗物质,才能解释这种差异。并且令她惊讶的是,所需引入的暗物质的总质量,要远大于被观测星系中已观测到的星体质量。
然而Rubin的这个开创性的工作,事实上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同行的注意。她自己也在随后的博士论文研究,和再后的职业生涯中,转向了比较主流的、不太冒险的星系光谱学研究。但是在1970年左右,她又转回了自己的暗物质研究,发表了一些新的实验证据。这些结果也逐步为其他实验组证实。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当年的硕士论文结果才终于逐步被学界广泛接受,即:星系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的未被观测到的暗物质。
随着暗物质(或者准确的说,没能被所用仪器观测到的物质)存在的事实逐步被接受,不少天文学家试图利用新的探测技术,即不同波段的光子探测器,去观测天体。此前,绝大多数的天文观测是利用可见光波段的望远镜。可见光波段,大约从400nm到700nm,对于整个电磁辐射光谱来数,是个非常狭窄的范围。电磁辐射波波长可以是任意长度。例如:日常的收音机波长数十米;手机所用的信号波长数十厘米;X光机所用的X光波长约为十亿分之一米等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步发展和建立了大量的红外、远红外、射电、紫外、X光、gamma光等波段的天文望远镜。天文学家在这些新的波段内,试图探测那些在“可见光”波段内的“不可见”的暗物质。但是这些搜索都被证明是徒劳,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所处的宇宙大部分是由神秘的暗物质构成。
暗物质组成之谜
暗物质会不会是由一般的重子物质构成的呢?宇宙中存在着光度非常暗的天体,例如行星、中子星、黑洞、衰老的白矮星等,它们可能因为发出的电磁辐射较弱而没有被观测到。但是,假定暗物质主要是由重子物质组成与天文观测事实有很大的矛盾。事实上,如果假定了目前重子的总量,那么理论上可以推算出在大爆炸初期形成的氦元素的丰度;如果假定暗物质大部分是由重子物质构成,将导致氦元素观测值与理论值的极大不符。除此之外,重力透镜等试验观测也同样表明,不发光的暗天体,根本不可能达到发光物质总量的十倍之多。综合种种天文观测结果,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重子物质总量不可能超过宇宙全部物质的6%。
既然暗物质的主要成份,不可能是由重子物质构成,那么理论学家试图构建新的模型,推测暗物质的可能成份。一种粒子,如果能作为暗物质的候选者,必须具有相当长的寿命,并且不可能参与强好像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因为如果暗物质寿命较短,由于暗物质的总量很大,暗物质的衰变产物将会相当多,那么暗物质早就被探测到了。同样,如果暗物质粒子参与电磁和强相互作用,因为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都非常强,那么暗物质就不可能那么“暗”了。目前比较热门的是暗物质候选者有弱相互作用重粒子WIMP(Weak Interaction Massive Particles)和轴子Axion等等。WIMP和Axion都仅参与重力和弱相互作用,因此使得它们如同中微子一样,畅通无阻的穿越探测器,几乎不留下痕迹。这就给观测这些鬼魅似的暗物质粒子造成了难题。必须要特殊设备和环境。
搜寻暗物质
暗物质探测是目前天体物理和粒子物理的热门研究领域。在地球上,由于无时不刻都有大量的宇宙射线轰击大气层。它们中间的一些,可能到达地表,甚至深入地下。由于暗物质与作为探测器的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几率非常小,因此如果在地表进行暗物质探测,大量的宇宙射线本底就会淹没掉暗物质产生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直接探测暗物质的实验,一般都置于地下深处。它们利用地表的岩石(或者冰层、水层等)屏蔽掉宇宙射线带来的本底信号。例如:意大利的大撒索国家实验室(Gran Sasso National Laboratory)和中国四川的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都是建在山体的隧道内;美国的DM-Ice实验,是利用南极的冰层做覆盖,屏蔽掉宇宙射线本底。锦屏山位于四川西昌西南约90公里。这里,雅砻江以“几”字形在锦屏山区流过。为了开发当地丰富的水电资源,二滩水电站修建贯通了一条隧道(在“几”字形的下部)用于引流发电。这条隧道全长约18公里,隧道离峰顶垂直距离约2500米。这些山体岩石的屏蔽宇宙射线的效果,相当于约7000米深的水层。这是目前世界上当量屏蔽层最厚的实验室。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暗物质探测提供了理想的场所。目前已经有两个寻找暗物质的实验进驻该实验室。一个是以清华大学为首的CDEX(China Darkmatter Experiment)试验,另一个是以上海交通大学为首的PandaX暗物质探测实验。
对暗物质的另一个重要候选者轴子(Axion)的探测则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轴子可以与强磁场相互作用,生成可以被探测到的光子。例如,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CAST(CERN Axion Solar Telescope)实验采用9.5Taslas的强磁场,用来探测来自太阳的轴子。在太阳的中心,电磁场非常强。如果轴子存在的话,当太阳内部的X射线被电子质子散时会在强场中产生轴子。这些来自太阳内部的轴子会和中微子一样轻松的穿过太阳,发射出去。当轴子到达地表的CAST探测器后,会与CAST的强磁场相互作用而生成易被探测的光子。同类的实验还有意大利的PVLAS,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ADMX(Axion Dark Matter Experiment)等。
在篮球场上,当运动员甲抛球到运动员乙手上时,两个运动员先后都会感到力的作用,而球在其中扮演了“力传递者”的角色。基本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如此。两个粒子相互作用可以通过交换“球”,也就是介子来实现。轴子可以扮演介子的角色传递相互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不同于已知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重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因此被称为第五力。通过测量两个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异常,可以探测是否有轴子存在。例如由美国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上海交大合作研究的极化3He实验就是利用此特点。如果轴子存在,极化3He原子核的核磁共振频率将会有微小的变化,通过对3He核磁共振频率变化的研究,可以推知是否有新的相互作用,甚或是轴子的存在。
除了上述探测暗物质方法之外,还有大量其它的方案。例如利用传统的高能的加速器,其所产生的环境可以模拟接近宇宙大爆炸最初时刻的状态。对于数据的精确分析,可以抓到那些偷偷溜走的“暗”粒子。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试图抓住这个神秘莫测的幽灵粒子。
李政道先生曾经指出:21世纪初的最大物理问题是暗物质暗能量的来源。我们居住的这个宇宙中,竟然有95%以上的物质和能量,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来源和组成!这无疑是对人类好奇心的最大刺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理性的光辉将再次照亮这个目前黑暗一片的领域,暗物质那时也将不再黑暗。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自豪地对暗物质说:你是某某;从是某某处来;将会到某某处。
学者小传
符长波,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特聘研究员。1995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近代物理系。其后加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从事核物理与核技术研究;2007年获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做博士后研究;自2012年加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目前主要从事暗物质探测、核天体物理、放射性核束物理研究工作。在暗物质研究方面,参加PandaX暗物质研究计划。PandaX是以直接探测WIMP暗物质为目标的,位于四川锦屏山地下实验室的大型暗物质探测计划。在探测暗物质其它候选者方面,首先提出了利用极化惰性气体核磁共振的横向衰减时间方法研究轴子Axion存在的可能性。通过结合其它核磁共振指标,在亚毫米尺度上,给出了Axion自旋相关相互作用的最好约束。在放射性核束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首次观测到N不等Z的核素内的alpha集团;观测到Ne18*双质子发射等重要结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50余篇。
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原文: http://news.sjtu.edu.cn/info/1022/133481.htm